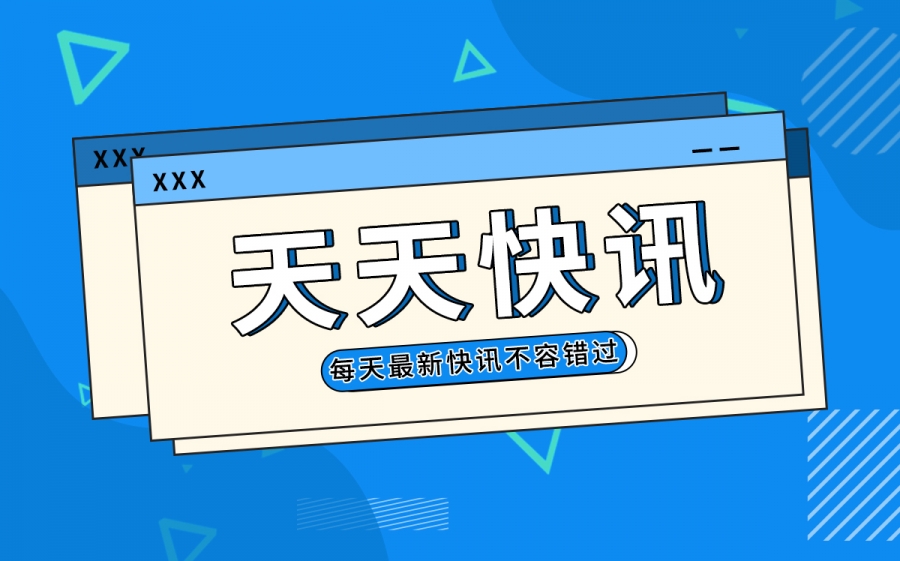作者:艾华
我看到了石板的姿态。
是在村上人家屋顶上,一块块的石板,以碎小而矫健的身姿,迎风而起。
 【资料图】
【资料图】
说鹰太雄阔,太伟岸,没有庞大的躯体和深远的目光;麻雀又太小气,支不起它的风骨,还是喜鹊吧,最符合它的气质,如同村上的夫妇,木讷憨厚,一辈子只知道埋头对着自己的窝缝缝补补,却仍有在空中扑腾翱翔的姿态和决心。
同样,飞翔的石板有一颗博大的心,全身不着寸缕,却用尽自己力气,趴在人家屋头,撑起屋檐下的一方烟火,并让这无穷无尽的烟火成为村庄弥久深远的气息。
这石板还自带了颜色,灰色中带点明艳,那是它刚出土时的颜色,有着对世间懵懂的向往,后来盖在屋顶上,风吹日晒,那点明艳,全都暗了,灰就成了村上永久的底色。
应该是草木灰的颜色,也不知道它们谁跟谁混了,石板、草木,村人,三者穿插来往,日常交错,时间久了,石板、草木有了村人的气韵,村人也染上了草木、石板的姿态,这是一种直接进入生活的姿态。
说起来,起屋盖房,在当时的村上,瓦是有些昂贵的,而且稀少,村人也只好就近取材,也不知是谁发现了石板可以盖房,于是石村所有的房屋,全都盖成了石板。还有碓窝、猪槽、水缸,都是由石头打制而成,整个村都是石头、石板,时间久了,就成了村的脸面,那就干脆让村也改了名字,石板场。
这脸面,被村人带了出去,在外和人摆经聊天,一开腔,人家就摸清了你的锅底灶门:你那里产石板。这脸面成了村人刻在骨子里的印记。
其实也不是整村都有,石板也只有特定的地方——长岭才有。长岭是绵延几里路的树林,荒无人烟,一条羊肠小路从林中穿越,小路用石板铺就,树木森森,六月天都见不着太阳,里面聚集了各种鬼怪传说。
三爷爷就说了,长岭是条阴街,每晚都有阴兵过街,听到山摇地动,喊杀声震天,却硬是看不到个人影子。并且活灵活现地说,村上某某人就在那里撞上阴兵过街,赶场回家走到长岭上,那时太阳已落土,只听到耳边枪炮声响作一团,此时正在树林中央,退不得,进不得,只有毛起胆子向前冲,回到家,在街上买的一把面条成了粉末,人也晕死过去,据说是被阴兵踩了的,从此那人独自一人不敢进长岭。
那时去学校,就要穿林而过,一进树林,就觉得阴风嗖嗖,浑身汗毛倒竖,任何的风吹草动,我都会把它们想像成阴兵的脚步声,结果是越想越害怕,头都不敢回了,一口气走出长岭,出得长岭,全身汗如水泼,透湿衣裤。
林下多奇石,也不知是不是吸收了长岭独特的气脉,这里的石头就长成了独一无二的青石。层层石,千层石,而石板也不用挖,而是“起”,“挖”太用力,薄薄的石板承受不住,就容易碎,得先用钢钎撬松,再用燕尾子轻轻的“起”,石板才能保持完整。
“起”石板,有讲究,起的不好,出来的石板不是这里破一块,就是那里损一坨,乱七八糟,好好的一山石板就起废了。
石板场的石板,只有二伯最会“起”,长衫撩到旁边腰间扎起,穿双偏耳草鞋,口含叶子烟,一弓步蹲起,先用挖锄四周挖薅一下,查探一番,再选中一处,钢钎撬几下,然后用挖锄轻轻掏空周围浮土,一块块厚重的石板就被刨出来了。二伯捏着钢钎,头微微上扬,一脸的自豪:你们不晓得么,这些个东西,它是有意头的,你不摸清意头,那你就搞不成事。就像田里的庄稼,你看那些洋芋、红苕,哪个没得意头?那些山长的有意头,水流的有意头,石板也是有“意头”的哟。
对了,这个“意头”在村上随时随地出现,村上人处处都在说意头,犁田打耙,要顺着意头,牛才不会乱跑;起屋接卯榫,木料会顺着意头。在家扭苞谷籽,母亲把苞谷坨的籽拧几行空下来递给我,说,顺着这个意头扭就行。我不懂什么是意头,却天天在意头里来来去去。
上学了,书本里没有这个意头的解释,字典里也查不到它,但是村人一用就是一辈子,就像村人手中的农具,口中的一日三餐,随手随口,然后又口口相传,传给下一代,下一代的下一代,再传。
传去传来,连村人的生活都有意头了,小婴儿生下来,抱着晒几个太阳,跟着大人带到田间地头,吹点风,这是顺风长哩;长大了,在世间进退有据,混得风生水起,村人竖起拇指:这就叫一个顺趟;老了,儿孙满堂,享天伦之乐,看一大家人闹闹嚷嚷,和人扯白聊天,背着手自豪地来一句:唉,耳顺之年了哟。这一切,都是顺着了人生的意头。一眼望去,地里的庄稼,长了一茬又一茬,新生命的意头还在那毛茸茸地拱着。
我手举一块石板,在那光溜溜的石板上反复查看揣摸,我以为意头就是长在石板上的,是一种图案或者是其它附着物件,可翻来覆去,石板除了纹理,除了颜色与灰尘,再没别的了。
二伯还说了,这石板啊,是土里生土里长的东西,你不能格里份外。就是你不能按你心中的所想去要求它有什么样子,它是什么样子,你就只能依着它的样子来完成。
这个我知道,是说它们都在向着自己的方式生长,就像是切肉时顺着的纹理,就像向日葵使终向着太阳的方向。你尊重了它生长的方式与习惯,它也才会回馈你想要的,做事时,先看一下,看清它的方向方式,顺着它的意头,如同老母亲哄孩子般,捋顺它的气,遂了它的意,你才能做成事。你若不按意头,不遵守它的方式,那你就是瞎子抓麻糖,越扯越糟。
果然,顺着二伯说的这个意头揭,那些石板犹如被打开的宝盒,顺顺当当,源源不断地被起出来。
我们也和大人一样,已经起了很多的石板出来。
大人不让我们用燕子尾,说那东西太危险,掌握不好,在石头上一磕,稍不注意就会挖到脚,挖锄又用不上。小孩子如果想做一件事,大人的阻止一般是不起作用的,我们的办法就是用手抠,或用木棍撬,轻轻松松就将石板掏出来了,顺着石板的这个意头,我们一掏一大片。
可到底都是三心二意,不一会儿就掏得不耐烦了。实在觉得无趣,直起身,看到远处几头牛羊在偷吃人家田里的庄稼,这可给我们找到了乐趣,于是拍起巴掌,跳着脚喊:牛儿吃麦子,不——要——油——盐!!羊儿吃麦子,不——要——油——盐!!哦——嗬……
声音撞在对门山尖上,又折回来,再荡开去,满坡满岭都是我们的喊声,偷吃的牛羊似乎也听到了,不过它们还是欺我们太远,管不到,只是不以为然地甩着尾巴,摇着头,挑衅我们般,走一步,捞一口,再慢吞吞地离开。
恨得我们咬牙切齿,真想跑去把它们撵回圈里。
实在无趣,就找鸟儿吵架。
这是常事,在村上,没有不和我们吵架的鸟,什么黄布罗,沙和尚,就连苦雀,你只要跟着它喊三遍,就会学得它火起,声音就会越喊越大,它就会跟你急。这些鸟俨然就是村上的半个主人,从不拿自己当外人,相反,在它们眼里,人才是外来的入侵者,挖山断石,砍树伐木,已逼得它们的家园往树林深处躲了又躲,藏了又藏,忍无可忍, 它们就再不会容忍你的半点挑衅,你只要惹到它,它一定跟你吵到底,寸步不让。
我们最喜欢学的,就是那种我们叫“水罐罐”的鸟,学名竹鸡,一到傍晚,就叫得格外欢。
太阳只剩下一半,要落不落地,挂在山坳上,原先嚣张的亮黄也变得温柔起来,却又是个吝啬的庄稼汉,抠抠卡卡,只给村庄披了半身的金纱,上半部分一片柔黄,下半部分青影重重,弄得村庄也跟着半喜半忧起来,屋顶上的石板披了一身橘色,摇头晃脑地看着屋檐下一脸铁青的阶沿,暮色从河沿口升起来,阴影在群山四下散开,慢慢将两种颜色融为一体。村上,炊烟从家户人家屋顶的石板缝里腾起来,晃晃悠悠地往上升,它们飘荡在村上,如同一顶巨大的帷幔,守护着这辽阔大地的人间烟火。趁着这最后的亮色,村上的一切都要归位,人要回家,狗要归窝,牛羊归圈,各种鸟儿也要上笼了。
大概是要庆贺这归笼时刻,竹鸡比任何时候都要显得欢快,它在树丛叫一声:水罐罐,我们就还它一句“丑八怪”,它叫一声,我们就还一声,再叫一声,我们再学一声,喊得它火冒八丈,越叫越急“水罐罐,水罐罐……”叫着叫着就叫成了“丑八怪、丑八怪……”声音也越叫越密,我们也喊越快,喊到最后舌头打了结,喊不转了,那“水罐罐”也喊得没了气儿,喊得变成了夹舌子。大人就说,这水罐罐喊晕死了,这时就好捉它哦,说归说,到底还是没人去找这鸟到底藏哪儿了。喊得天黑尽,竹鸡再也不出声了,才在大人的哄笑声里结束骂战。
一天的采石时间就在这欢快的吵闹中结束了。我们依然长久地与这些鸟和动物们相处一起。
起好的石板,不能立马用,要堆在一起晾一晾,而堆石板,也是有讲究的,要一块一块的倒立着,并且堆的也是个倒三角,估计是倒着好让雨和风把石板上的泥抹掉吧。晒几个太阳,淋几场雨,该青的青,该白的白,石板什么纹理,什么性格,什么路数,瓦匠师傅心里才有底,盖屋时才会物尽其用,保证让每一块石板都用在点上。蹲在人家屋顶上,得有好个姿态才行。
过段时间,石板就晾好了,晾好的石板在背的时候,要一块一块地放,背回来时要一块一块地取,全程小心呵护,容不得半点马虎。即使有碎的石板,主家都舍不得扔,留着嵌在场坝里,或嵌在自家屋周围的路上。原先土里土气的院子,也居然有了几分贵气。
而石板,不仅有姿态,也还有故事。
谁说不是呢,那一块块石板,它们的形成、生长、启用,都是在村上的故事里浸润出来的。钢钻一拿,将那些厚厚的石块剖成一块长的或方的形状,那些埋藏在石板里的秘密,就全都流出来了。
不信,你去村上打听打听,哪家屋里起屋上梁盖瓦没得点故事?哪家屋里嫁女娶媳没藏点嘀咕? 还有那些养儿育女的,谁家没得个几箩筐几簸箕的事?
起屋造房,是村人一生期望并为之奋斗的目标。穷其一生,为的也就是上有片瓦遮雨,下有破塌容酣。
可四爷爷家不一样,我每次去放牛,路过四爷爷家,牛总要把四爷爷家屋上的茅草捞两嘴。四爷爷一个人住,两间茅草屋摇摇欲倒。我家的牛就喜欢扯他屋上的茅草吃,不知是不是牛也喜欢烟薰火燎的岁月味道,连一口干茅草都能嚼得唾沫横飞。
四爷爷看到也不恼,只是嘱咐我要牵紧牛绳:“再把我屋上的草扯吃了,就让你屋大人给我换成石板哈,”四爷爷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,我把头啄得如点水雀“要得要得,”下一次路过,牛还是要捞嘴。四爷爷还是笑,就像挂在树丫上的太阳,明晃晃的。
我是巴望着四爷爷把茅草屋换成石板屋,而且,四爷爷明明自己就是瓦匠师傅呀,给人盖屋,在屋顶上往来穿梭,如履平地,盖的屋顶多年不坏不损,该直的直,该硬的硬,一身好手艺。
四爷爷有次喝醉,拍着胸脯“不是我吹,这村上手艺好的瓦匠师傅,哪个不是我带出来的哟。”
旁边人一脸折服样。可我想不明白的是,四爷爷有这么好的手艺,给自己家换石板不是小菜一碟吗?可四爷爷始终不换,两间茅屋始终是要垮不垮,旁人看得心惊胆颤,生怕四爷爷哪一天就在茅屋里出不来了,而这要垮不垮的茅草屋陪伴了四爷爷好多年,最后直到他茅屋倒塌一半,又到他去逝,始终没换上石板。
村上的老人,平常不多言,但总是会在酒后来一声长叹:老四这一辈子……可惜哒。
四爷爷的故事,就在村上欲言又止的叹息里,让人知一半猜一半。
说是四爷爷年轻时,说成了对门梁子上的一门亲事,双方商量好了,结婚的时候,女方给四爷爷把一间屋的石板,好盖新房,四爷爷有了动力,不分昼夜,累死累活地打好两间屋的土墙,按四爷爷的打算,盖一间石板屋当新房,另一间盖茅草当灶屋。
眼看婚期临近,四爷爷找了几个帮工,欢天喜地去女方家背石板,到得梁子上,老丈人青分黑脸“你有好大的底子就搭好大的架子,只盖得起一间屋就盖一间屋,你还一间石板屋一间茅草屋是比照着出丑,还是嫌我给你的石板少哒?”
人前人面,四爷爷一口气憋在了梁子上,也在心里憋下了一道梁,回家躺了几天,水米未进,从此不再说亲,独自一人在茅草屋进进出出。
村上人说,四爷爷也是固执,人家姑娘后来都主动撵来了,他却又把人给撵回去了。
“要是我……”那人顿住,瞟一眼,周围空气里流荡着一股股的神秘。
我们听得个糊里糊涂,反正只知道四爷爷没成家,一个人过了一辈子。
不过呢,像四爷爷那样的人,毕竟是少数,“人这一辈子,都是在跟自己较劲,有那个能力的,就多跟自己较点劲,没得那个能力的,就少跟自己较点劲,反正无论怎样都是一辈子哟。”
吴大爷说这话,就像是在给村人比着箍箍画鸭蛋。
辛苦劳碌半生,一根根沉重的木头扛回来,一块块沉重的石头背回来,磨得肩膀上的老茧硬如铁坨,腰杆压弯了半截,才终于备好了起屋的材料,请石匠、掌墨师把屋架子立起,封出房屋框架结构,又请木匠上梁钉檩,最后才请瓦匠盖屋顶。
盖屋也同样隆重,也要看日子。选好黄道吉日,瓦匠师傅才得进门。盖石板,是个过细活路,也要技术,盖瓦的师傅不一定能盖得好石板。只有常年累月与石板打交道的师傅,手上一掂,就捏清楚了石板的东南西北和它的意头。盖的巴头巴脑的肯定不行,那样会塌了主人的运气,一辈子做什么事都窝火。
得盖出石板的气势、格局。一块块,一层层,该低的低,该拱的拱,该有气势时就要让它飞,还要估计它的抗风能力,与檩条的搭配,下雨屋檐水的落处,石板与石板之间的接头。要将石板铺得高低叠压,错落有致,宛若一片片鱼鳞铠甲,各自为阵,却又是铁板一块,既要通风透亮,又要滴水不漏,这才是一个好瓦匠。
盖石板也是个慢活路,慢工出细活,不能得急,得急也不行。手艺好、手脚快的师傅一天可盖两间屋顶,手脚稍慢的师傅就只能盖一间或半间了。其实也看不出手艺差距,他们的动作都是一样,轻手轻脚,慢条斯理。
我倒不觉得那是他们手脚慢,手艺不精,倒是在和石板摆经聊天,切磋手艺。看嘛,师傅就在唠叨了:先前放下去,一看又还行,这时你又翘起来,来嘛,给你塞塞,顺手往石板缝里塞点小碎石板,前凹后翘的石板立马规矩了。还有的石板和檩条不配合,意头不同,各顾各的,瓦匠师傅就拿起小锤,把石板的边边角角敲一敲:边角不能太锋利哈,还是要圆润一点,然后再把檩条拨一下:退一退,不能太紧了,该松的时候还是要松一下嘛。一番叮叮当当敲下来,该退的退,该让的让,一个二个都服服帖帖。
往后即使有个风雨,也能抱成一团,相安无事。
这泰然自若的姿态,让我有十分的理由相信,村人的言行举止、处世为人,都是跟着这些石板和檩条学的。
接下来的点睛之笔,就是屋脊的装饰了。在村上人家屋脊的正中心,都要拱一个图案。盖一个丹凤朝阳,幸福的生活滚滚来,拱一个三阳开泰,主家事事都吉祥。不过这样心灵手巧的瓦匠师傅,村上倒是很少,石板屋盖得最多的样式,就是人字脊,品字形。
这人字脊就是在屋顶上拱出一撇一捺,简单粗糙,一如村人简单粗陋的心性,远远地看,如同负重的村人歇在打杵上,叉着腿,端着身,踏着重重的山水。而它也就真端着这个身子骨,立在屋脊上就是一辈子,风吹日晒,狂风暴雨,青苔一层、灰尘一层、风雨一层、冰雪一层,慢慢地,这人字也就凝重起来。
主人老去,或者搬走了,它还在屋脊上,纹丝不动,似是村上初识字的顽童般,揣不透这个字的笔画与意义,只得一遍遍仿写,一次次记忆,揣摸得久了,这一撇一捺就有了气势,左踏大地,右跨山河,如钢钎大锤般,牢牢地钉在了屋脊上,除非被疾风暴雨打落,跌在地上,人字倒下,碎成一地石渣了,却依然保持宁为碎石的那身姿态与风骨。
不知为什么,看着那些碎石片,我总是想起四爷爷。想起四爷爷那张皱纹深深,却如太阳光一般耀眼的笑脸,还有那眯成一条缝的眼睛,不动声色,却又明察秋毫。
品字形屋脊就是上一堆石块,下两堆石块,比起人字脊的轻巧与简洁,品字形就是端庄与厚重了。
我常常望着大伯伯家的那个品字形屋脊发呆,想不通他们家的品字为什么要比别人家的石板堆得高,堆得多,远远地就能看到那个大大的品字,如书法家在挥毫泼墨,很有气势。
问大伯这个品字形的意义,大伯咳嗽一声,手指屋脊:喏,这石板啊,你看像不像电影里那些手无寸铁,却又在战场拼杀的英雄战士们;这品字形嘛,就是一面旗子,旗子一挥,战士们就冲锋陷阵,前头哪怕是刀山火海,也要往里滚。
一只田叉拖着长长的尾巴闹喳喳地飞过山头,又飞往庄稼地。我歪头想了半天,只忆起电影里的红旗招展,刀枪大炮,怎么也和面前沉默的石板扯不上关系,但看着大伯严肃的神情,我不敢多问,只好在心里来回数着飞过的田叉。
其实我心里住着一个更大的问题,大伯家为什么不全换上石板屋?就按他堆在屋脊的那个品字形,都够他盖上另一间石板屋了。
后来我也问过大伯,可大伯笑得高深莫测。他的三间土墙屋,两间盖茅草,唯独厢房,盖了石板屋。后来才知道,大伯伯最小的儿子,当年去参了军,大伯给两弟兄分家,把厢房分给了小儿子,说怕他到时回来。
他的小儿子,我们喊家哥的,直到大伯伯去逝,都还没回来。
这件事,村上人已经议论了很多年。有说家哥当年参加的是解放军,早就在战场上牺牲了。有说家哥已在外安家,不想回来了,还有说家哥可能是成了土匪强盗,没脸不好意思再回来。
七说八不一,最终也没有结论。大伯在世时,会气冲冲地和人去理论,争得脸红脖子粗:“他就算是强盗土匪,只要他回来,就还是我儿……”那样子,恨不得上去和人拼老命。大伯去逝后,所有的争执也烟消云散,只有大伯家屋脊上的品字形,一年年地沉默着。
家哥回来,是在大伯去逝多年后。当年风言风语的村上,已有大半人老去,没人记得当年的议论,村上用了讶异和热烈来迎接他。听说家哥已从部队转业,在单位上班了,并且是原先在一场战争中受了伤,才转业回来的。
家哥回来时,秋风正从村上掠过,很多人家的屋顶上,瓦匠师傅正在忙着捡漏,迎接下一个季节的到来。长风起伏,碧空如洗。
家哥在石板屋前长跪不起,头在地上叩得咚咚响:“爹呀,你的用意我知道,这么多年,我没忘根,没给你丢脸呢,你咋就不等我回来……”那时双亲都已去逝,家哥哭得一塌糊涂,男人的泪如刀,剜心剜肺地割,疼得一村的人眼泪水跟着哗哗掉。
家哥最后没要那间留给他的石板屋,但吩咐大哥别拆,他出钱,让大哥隔几年请瓦匠打理一下,大哥也略会捡漏,开始那几年,就由着大哥慢手慢脚地打整。一间石板屋,他在上面整整三天,下得屋来,一身的灰,糊得只看到两个眼睛子在转。每次看大哥蹲在屋脊,就如同看到当年的大伯,沉默木讷,却又高深莫测。
后来,大哥老得走不动了,瓦匠师傅也一个个老去,村上也实在找不到会捡漏的瓦匠了,这才作罢。但那个品字形屋脊,这么多年还在村上矗着,不折不缺,隔着厚厚的时光,打谅着世间的来来去去。
其实在村上,盖品字形屋顶的人家还蛮多,有的就是三两块石板堆一下,显得有些单薄,大都是中规中矩,像大伯家堆的那般厚重的很少。
但无论厚薄,村上都把这个品字从屋脊刻在了心里。养儿育女,审事度物,都暗暗以品字来度量。
那时的村上,一户人家大都是四五个孩子,团方四邻,大七八户,都是晓得彼此锅底灶门的人,几斤几两,早就被人掂得清清楚楚,惟有在儿女身上,才有着让人摸不准的底气。村上少年,一个二个都是那山野中的小兽,桀骜不驯,争气是他,败家也是他,家教不严,一出门可能就被人戳了脊梁骨。明面上,大家似乎都一样,穷困、艰难,暗地里,却各自暗暗攒着劲,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,自己这一辈子没混好,但下一辈,绝不能落人后。
他们生怕自己家的儿女行差踏错,给自己丢人,给祖宗丢脸,在村上,除开柴米油盐,教儿训女才是他们的人生大事,哪家出了不孝忤逆儿女,轻则一顿打,重则拎着他去祖宗坟前跪着受罚:“你憨点穷点都行,出去不要弄那些歪门邪道,莫把那个人品给我搞坏了,人品败坏,那就是根烂了。”
村上的孩子,都是在父母的竹条子里撵着长大的。“棍棒底下出好人”是村上奉行的亘古不变的道理。哪件事情僭越了,哪点规矩败坏了,哪点礼性没跟上,品字压上头,直接一顿棒喝。
这是真的,你只要在村上转一圈,哪家都是在训孩子。哭天喊地乱作一团,村上那些老人看着打孩子,居然无动于衷,“这些个娃娃儿就好比是才生的牛儿,到一定的时候就要穿牛鼻,上枷担,要不然不知天高地厚,不敲不打,他不晓得生活的意头。”一幅稳妥妥的样,把我们气得,恨不得扒了他家的屋顶。
不过,这种教育方式也搓磨了我们的心性,抗打压能力超强,往后人生路上,风雨挫折、磨难困苦,根本不值一提,就像村上屋脊跺的那些石板,顽强、坚韧。
这乱哄哄的村庄,虽是状况百出,可它一直都遵循着自己的方向和意头。如同一只扬帆出征的船,嘈杂拥挤,摇摇晃晃,却始终望着灯塔的方向。
大伯家的品字形屋脊,就是这凌乱村中立起的一座灯塔。
后来还听说了家哥的一点事,他因为是队伍里扛旗子的,为了保护红旗而受了伤,但即便受伤,也没让红旗倒下。
忆及当年,我才明白,大伯为什么要把石板比作战士,品字形屋脊比喻成旗手了。
家哥我从未见过面,他很少回村,我们也互不认识,其实村上有很多人不认识家哥,村上有关他的记忆,都是只言片语,他的事迹,我也只是略略听说。
后来的村人,教育儿女,最多的一句话就是“你看看人家,那才有出息,是个大英雄。” 这个很少回村的人,却给石板注入了力量,而石板,再用这力量来浇灌村庄。
人说一方山水养育一方人,石村,多了一样,石板也养人。
石板滋养的人走出村庄,走出石板屋。
我们和父辈们最大的不同,就是不再满足于田野里那些洋芋、苞谷的价值。我们是年轻一代的农民,却不在执著于挖锄与庄稼,泥土与田野,藏在身体里的那些石的骨质,开始蠢蠢欲动,开始由内向外生长。
来叔是和我们从小玩到大的玩伴,他和我们年岁相当, “少年叔侄当弟兄”,人前人面,我们跟着村人一口一个的 “来哥儿”叫着,他也不知事,整天和我们玩得灰头土脸。我们一起掏鸟窝,一起打蜂包,一起摘悬崖上的八月瓜,一起挨大人的训斥。一直到现在,我都还不习惯叫他“叔”。
童年玩得最多的游戏,就是用石板盖房子。来叔是盖房子的高手,他劲用的巧,一般能盖到十多层,差不多有一人多高,就像一层层的塔。并且也结实,无论我们在旁边怎么捣乱,这房子依然稳如黄钟。
我觉得,来叔的梦想就是从搭建石房开始的。
来叔后来在城市从事建筑工作,室内设计、装潢,开起公司,日子过得风生水起。走出石板屋的后来还有梅子、姣姣……
而石板屋就像我们一样,也在发生着变化,它们经历了从石板到瓦,然后再到现在五颜六色的琉璃瓦,石板屋的阵地越来越少,却愈发坚固。每次回去,看着那些依然守在村上的石板屋,它们牢固得如同我脚下的这片土地一般,守着它的家园,亦如同老父母守着他们的老屋,倔强地以此来表达他们生命的轨迹和生活的姿态。也为了让我们,那些飘泊在外的人,仍怀有小鸟初飞般的信念,顺着村庄的意头,不知疲倦,一次一次扑棱着飞回故园。
从石板屋原先出走的人,很少,也不再回来,而现在走出的人多,回来的也越来越多。
近来,看来叔常常往老家跑,一车一车地往他公司运东西,他说这是高价回收的旧石板。问他回收石板干什么,来叔笑着说:“你不知道吧,现在乡村人家盖房实行把这些石板抛光打磨,再一块一块散嵌在墙上,大家欢喜得不得了,说这东西很有意境。我把石板给他们加工,然后再拉回去。”
想起来了,村上的何二哥在深圳打拚多年后,最近回到老家盖房子,拉回一大堆油光锃亮的石板,把它们当宝贝似的。我还以为他是要怀旧,再来盖石板屋呢,原来是这个用途。
我愣了半响,才问来叔为什么不直接去当年挖石板的地方起一山石板,却要大费周章,满村跑着找石板收,来叔笑得神神秘秘:“这你就不知道了吧,只有年代越久的石板,才能磨出那种古朴的东西,那些新石板,没经过风雨,一上打磨机就碎成渣了。”
我听得呆若木鸡。从小在石板堆里长大的人,石板的一举一动,一招一式,都熟悉不过,竟不知,石板也是有意境的。
其实也不能怪我们,村人一直都不知道有这个词汇。只是在我如今的回忆里,那些困苦而又热闹的岁月里的回声才会有这些韵致。
当炊烟一缕一缕从石板缝里飘出,呼儿唤女的声音从村上响起,鸡犬相闻之声悠然相至,石板屋下的柴米油盐,鸡飞狗跳,生老病死,就成了村上永恒的意境。
岁月的车轮缓缓而过,如今,石板正以另一种崭新的姿态重新进入村庄。相较原先的粗糙简陋,它们多了几分讲究与精致,却初心未改,仍旧守着村庄的岁月,守着村人的烟火,守望着一个村的根脉和质感。而石村人,从一出生,就染上了石的特质。两者的生命长久互相依偎,互相晕染,时间一长,都有了彼此交融的生长气息,无论你身处何方,它都会像田里的庄稼,一茬茬地生长、发芽、拔节。
石板是村庄的意头,也是村庄的姿态,有了石板,村庄就有了思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