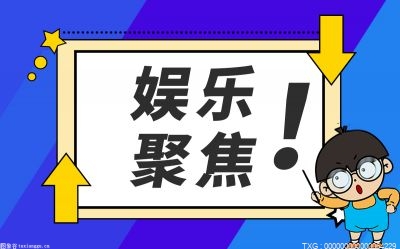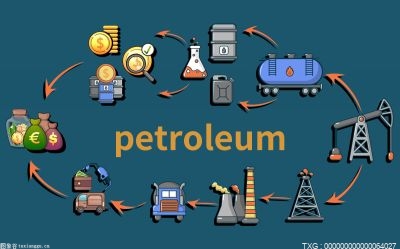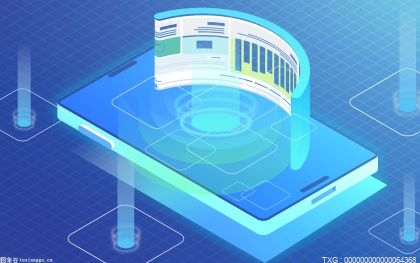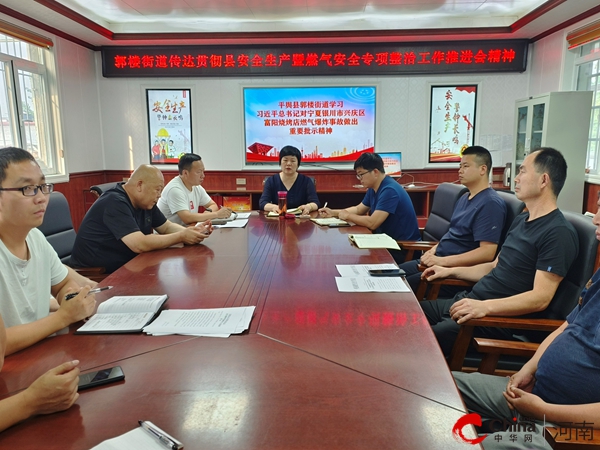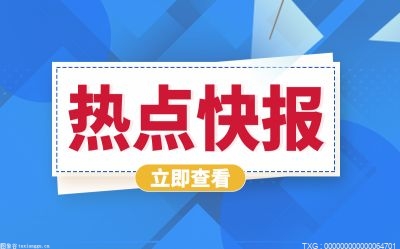羊城晚报《汕头文脉》7月3日版面图
 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濠江,古韵悠悠
□许巧如
在濠江畔,听渔歌悠扬;天马行空,看晚霞漫天;日落沉金,思人生苦短。濠江水长流不息,霞美庵钟声依旧,天光云影徘徊着几多人世沧桑,倾泻在江面,激荡的波涛,推风助浪,都付诸江底。
霞美庵,这里的地形就像一把利剑,一把从濠岛抽出来,刺向大海的宝剑,剑指南海深渊,问海;也像一只伸出去的手臂,拳头紧握,略带挑衅,欲与南海相较量,比力气,比魅力。
这里有渡口。古老的渡口是达濠人文初始时期就有的,最先抵达濠岛的移民就住在这地方。这里,最早是出海捕鱼的地方,也是对外联络的一个渡口,它曾经凝聚着多少捕鱼者及家里人期盼的目光。一艘艘出海捕鱼的船,承载着一家家渔人的幸福安康。曾经,这里是黄金水道,熙熙攘攘的船只、人流在这里如潮水般涌动,络绎不绝。那些海上船只从南海进入濠江,到达汕头。曾经在这里,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给濠江带来了繁荣的海上贸易,濠江,千金港,在这里闪耀着它的光芒。
这里有寨墙。临海建寨,形成后来的下尾寨。这些寨墙以前全是捶打而成,难以想象,当年,住在附近的渔人,为了守卫家园,他们是如何光着膀子、挥洒汗水,在这里用海水混合着贝壳用力捶打着泥浆,斑驳而厚实的寨墙凝聚多少人的汗水?现在,岁月吞蚀着墙泥,海风消磨它的容颜,如今连寨墙石也被挖掉了上百块。今天,所剩无几的寨墙,印证历史的变迁和风雨的洗礼。寨墙在沉默中继续老去。
这里有古庵。“未有青云岩,先有下尾庵”,下尾庵即是霞美庵。霞美庵,五百多年的历史,五百多年的霞光,映照多少人的身影?染红过谁的脸?霞光普照,庵中庵外的世界,披着同样的霞光。庵内,青灯、木鱼、素菜;庵外,渔歌、浊酒、鱼饭。他们在钟声中各具特色,各自精彩或各有其悲哀,故事应该很多。
凭江而望,江对面是美丽的凤岗,如栖息的凤凰。江岸有怪石嶙峋,“头戴石”,也叫牡丹石,形成“双凤朝牡丹”地形,再望过去,龟山和南山,一衣带水,茂林修竹,有地形若蜿蜒爬行的蛇,叫“龟蛇把水口”。相看两不厌,大自然的鬼斧神工,让一切景象如此美好和谐。
“青山依旧在,几度夕阳红”,最美不过夕阳红,那一缕缕、一朵朵的晚霞更甚。在霞美庵,坐看最美的霞光,放飞思绪,遐想联翩。此刻,你可以感受到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意境之美。你,或者就是那一片霞,或者就是那一只孤鹜。夜幕拉动,渔歌响起,晚霞归尽,看星月主宰的苍穹,亦辉映濠江。渔火点亮濠江水,夜晚,静静的霞美庵,淡淡的哀伤,游丝般慢慢流淌……
侨乡风光 邹晓东 摄
撑排人
□柯镇清
木龙伯年近八十了,身体硬朗,精神矍铄,就是门牙掉了几个,说话有点漏气。每隔一段时间,他骑着自行车来找我喝茶聊天或者下棋。每次进门的第一句话,就是问我有没有回老家。之所以这样,是问我在回家的路上有没有经过一个地方,一个他不止熟悉,甚至可以称之为第二故乡的地方,这就是——头塘村。
头塘村毗邻韩江。我如果选择沿江的公路回家,就会经过那里。多年以前,头塘村的江边有一个木材厂,准确地说,是一个转运站。彼时,木材扎成木排通过韩江漂流而下,直达潮州或者汕头。头塘村段的韩江江面宽广,水流相对平缓,这可能是被选为中转站的原因吧。有些木材也在这里做一些加工。记忆中,我小的时候经过这里,经常会看到一些工人赤裸着上身,汗流浃背地拉着锯来锯木。木屑飞扬,粘在他们黝黑的皮肤上。走过这个路段,空气中总是飘荡着一股木料的香味。木龙伯当年在这里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,以至于我偶然谈起回乡的路线,他都把我当是他乡遇故知了。
潮汕有句俗语:“一惨撑杉排,二惨挑鱼崽(苗)。”木龙伯喝茶的时候经常会提起,口气中却没有哀怨和无奈。在他看来,年轻时受点苦是应该的,能在年老的时候安享晚年,这一生算是幸福了。伴随他的口述,我的脑海浮起一幅幅画面:夏日的江面上,太阳热辣辣的,水流比较急。几个中年汉子拿着长长的竹竿分别站在大片木排的不同角落,时而将竹竿往水里一探,弓着身子用力将木排往江中撑去;时而拿着一条布巾擦擦身上的汗水。寒冬的江面窄了很多,枯水期的到来让江底的沙滩大面积露了出来。木排很容易搁浅,撑排的汉子有时得跳下江中用力将木排外撑。江水冰冷,他们似乎浑然没有感觉,只是在木排顺利漂流的时候才披上一件上衣。更多的时候,他们几乎都赤裸着身体,只在腰间围着一条遮羞的水布。如果穿着衣服,很快被水打湿,行动不方便,甚至,湿透的衣服还会擦破皮肤。就这样,无论寒暑,不管阴晴,撑排人在运输过程中日夜吃宿在木排上,披星戴月,风里来浪里去,将木排漂向目的地,其中的苦涩只有撑排人才能体会。
世事如棋局局新。头塘村的木材厂经历了兴旺,平淡以后还是没落了,旧址日趋破落,唯有江边的一棵木棉树依然茁壮。与木材厂一样,这棵木棉树是头塘村的地标,也是当年许多撑排人的挂念。每逢花开的季节,在距离木材厂很远的江面就能看到木棉的花姿,树梢丛丛簇簇焰火般的花朵犹如家中的明灯,照亮撑排人回家之路。
年年花相似,岁岁人不同。头塘村的木棉和撑排人见证了木材厂的兴衰。许许多多木龙伯走过岁月山河。花开花谢,棉絮飞扬,如今的韩江山清水秀,支流旁系里的小溪常见游人坐在木排上,悠闲地观赏两岸的风光。每见此景,我总不由自主想起头塘村、木材厂、木龙伯,还有木棉花开的日子……
故乡的荷塘
□张正
又到了荷叶田田、荷花盛开的季节。小区的那个小水池里,密匝匝挤满了高高矮矮的荷叶,微风拂过,艳丽的荷花闪烁其间。不时有清淡的荷香袭来。这还是故乡的荷吗?
在故乡,一个标本式的农家,有菜园,必有荷塘。
故乡属蜀冈余脉、丘陵山地,田小,塘更小。
水在故乡比较金贵,塘是用来贮水的,差不多家家户户有一小口。不是十里荷香,却一样丰富多彩。
谁说荷塘不也是菜园呢。菜园里有四时菜蔬,荷塘里的出项也不少:荤的有鱼、有虾、有蚌、有鳝,素的有茭白、有茨菰、有红菱、有水芹,自然还有荷藕。
最惹人爱的,就数荷藕了。
荷藕的性格是恬静的,四五月间,碧碧的塘面上悄悄地冒出那么一两支,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,说的正是这个时候。等它们陆陆续续撑起小伞,你心里多了一份期待——荷花快要开了吧?在故乡人的心目中,荷花是有灵性的,只能远观,不能采下把玩。可不是,连观音菩萨,也以荷花为宝座呢。有不懂事的孩子经受不住诱惑,糟蹋了荷花,被大人发现,一定会招来骂。
荷花被我们看作洁净之物,不容亵渎,荷叶也同样让我们怜爱。我们很少摘下荷叶玩耍。坐木盆在荷塘里采摘红菱,穿行其间,也是小心翼翼,生怕弄破了荷叶。我们最爱撩起一捧水,泼洒在荷叶上,看水星珍珠玛瑙般滚动、聚合。“从来不着水,清净本因心”,这是荷叶的本色。
也有年轻的女孩儿,连茎折下一片宽阔的荷叶,高高举起当伞擎着,赤脚走在阳光下。那时,荷叶映衬着她红扑扑的脸,她跟荷花一样美了。男孩儿喜欢把荷叶倒扣在头顶上,弄成凉帽的模样,荷叶下的脸蛋快乐而有生气。
“七菱八藕九茭白”,在说荷藕成熟的季节呢。农历八月,鲜藕上岸。故乡的荷藕,没有大规模的收获景象,想吃了,跟进菜园割韭菜一样方便。跳下荷塘洗冷水澡的工夫,用脚崴几下,崴着了,用脚挥去泥,一个猛子扎下去,冒出水面,一根湿漉漉还沾着黑泥的新藕正抓在手中。
藕可生吃,可凉拌,可热炒。稍稍讲究的人家,还会揣进糯米,烀熟,切成薄片,蘸了红糖吃。通常在有喜事办酒席的人家才可以吃到这样的细食。荷叶黄,莲子成,稍后的莲蓬也是我们孩子三餐后的小食,一粒一粒地抠出子,剥去软软的壳,丢在舌尖上,一咬,甜津津的。后来才知道,荷叶也可以入食呢,用荷叶蒸饭、烤肉,食物上添了淡淡的荷香,沁人心脾。
故乡的荷藕不需要专门栽种,也不需要特别料理,一年下了种,年年生新荷,岁岁有嫩藕吃。夏天的塘面上,挤挤的一塘荷叶,争先恐后向上窜,遮得塘水阴凉凉的。微风拂过,香气溢出好远。
夏日能采新藕,冬日能挖老藕,在特定的年代,荷塘在故乡发挥着储粮罐的作用。
荷叶田田,年年依旧,塘却在萎缩。故乡农户家前屋后的荷塘开始干涸淤平。荷不再遍地开花,随处可见。取而代之的,是零星的种藕大户,他们利用水源好的低洼地,经营一片又一片“叶香原是胜花香”的荷田。昔日的荷塘像是聚集到这里开会来了。还有高楼林立的城里,也增添了许多长满荷叶、荷花嫣然的景点,那算是来城里做客的荷吧,就像从故乡走出的我。
故乡的荷塘,沐浴着清风,摇曳在我的记忆深处,永远那么葳蕤。
眼前小水池里的荷,也娉婷多姿,我终究还是惦记着故乡的荷,和故乡的一切。
东湖时光
□林妙英
我的挚友小雪是东湖人。中学时代的我们喜欢手牵手在海边漫步,捡贝壳,看着船只在壮阔的海面上穿行,对着大海高声呐喊少年的梦想。海水涌上石头,长出一片片乌黑的紫菜,每一次品尝,都把家乡的味道深深地刻在心底;海浪拍岸,海鸥声声,每一声都是对游子们的归盼。
那年暑假,小雪盛情邀请我到她的家里做客。天还没亮,我们在睡眼惺忪间闻到米粥的香气,听到收拾工具的声音……原来是小雪的母亲准备去海边“落溪仔”。这活儿不仅要会游泳潜水,而且操作工具有诀窍。上午九时左右,小雪的母亲满载而归。小小的背篓里,装着各种贝类、淡菜,还有海藻类食材石花菜、紫菜,更有一些叫不出名的贝壳。小雪的母亲蒸上一大锅淡菜,味蕾就这样在美好的时光里绽放精彩。
闲暇时,我们打开冰箱。小雪的母亲早早就备好亲手熬制的海石花,晶莹剔透的,配上蜂蜜和白糖,我一口气能吃上三碗。小雪的家人总是乐呵呵地说:“英,喜欢就多吃点,不够就再做给你吃!”
从海里回来后,小雪的母亲又和工友们,赶着去做山工,或者泥瓦工。只要哪里有活干,她就往哪里跑。她的身影总是那么高大、坚强的样子,笑起来淳朴而温暖。我们吃的每一顿饭都感觉那么踏实而幸福。
说起小雪的父亲,他只在逢年过节才回东湖,大多时候都在香港和深圳之间往返,回家的时候,总是穿着黑西装白衬衫,拉着重重的行李,带来各种港货,俨然一副番客的样子。小雪像其父一样热爱学习,见识广博。小雪的父亲总要冲上一壶好茶,和我们两个小不点一起,讲述他最近在香港发生的有趣故事以及他的人生感悟。
小雪和母亲已经习惯了父亲作为番客常年在香港的日子,但家里的一砖一瓦、一针一线,无不是小雪父母共同经营的结晶。
多年以后,东湖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,变成以“菊”和“侨”为纽带的“和美侨乡”。多少游子、文人墨客因为它的底蕴慕名而来。而我,依然记得当初在小雪家里度过的快乐时光。
初夏之美
□戚思翠
粉嫩的春被几场和风暖雨轻荡柔涤后,悄然隐退了,夏姑娘便开始舒眉展姿、粉墨登场。钟爱初夏,寒意远去,炎燥未至,皮肤如筛上了一层软酥酥的光汁,每个毛孔里都舒展出欢欣的气息。初夏,宛若豆蔻年华的少女,清纯温婉,轻盈梦幻,一回眸,露出浅浅笑靥,令人陶醉。初夏,一如苏轼的《阮郎归》所云:“绿槐高柳咽新蝉,薰风初入弦。碧纱窗下水沉烟,棋声惊昼眠。微雨过,小荷翻,榴花开欲燃。玉盆纤手弄清泉,琼珠碎却圆。”
初夏,初恋般的芳醇。这时节,大自然以绿为主色调。林荫道上,高大树木,蓊蓊郁郁,绿意融融,生机勃勃,春意盎然。目光穿透绿树缝隙,天空湛蓝湛蓝的,那么深远,那么辽阔;路边荷塘,碧水澹澹,微波粼粼,游鱼历历,垂柳依依。出水荷叶,像撑开的绿伞,似层层绿浪,如片片翠玉,美丽动人。野生芦苇摇曳着一身碧衣,暗传秋波,送来阵阵清香,诱惑路人。艾蒿和毛地菜已长出来,叶脉分明,叶子反面的白绒,如霜一般。初夏的绿,比春天的嫩绿多了几分成色与厚重,但还不至于绿得沧桑,这种绿,不深不浅,多情妩媚,养眼撩人。处处都是美丽明亮的色彩,一切欲说还休,都袒露了出来,但还不至于太热烈,就如同一场爱情,没有早一步,也没有晚一步,刚刚好。
初夏,诗意般的曼妙。这时节,大自然遍地花开,恣意绽放,诗情画意,风景如画。徜徉在城市街头,满眼葱茏滴翠,各种花儿点缀其间,色彩缤纷,芳香四溢,装点着这个城市。樱花海棠已谢幕,杜鹃花也想藏起笑脸,陆续登场的月季花、玫瑰花、蔷薇……这几种外形难以区分的花,不是那种连绵一片的大红大紫,更多的是点缀,却以少胜多穿行其间,有一种流星花园的奇妙之感。除了彩花,还有各种素花,海桐、女贞、荼蘼、栀子花、白兰花、茉莉花……都是白中带着淡绿,这就给初夏添上一层极富意味的诠释。或许,初夏原本就是一位淡妆素雅的女子,她不施粉黛,只着一袭白长裙,但稍一顾盼,便摇曳生姿。初夏之美,美在万紫千红的生机蓬勃,美在绿意清雅的宁静幽远。
初夏,梦幻般的神奇。这时节,大自然以繁荣为主旋律。过了小满,草木开始繁茂,谷物籽粒开始饱满,但还不够成熟,故称小满。农人从庄稼的小满里产生夏收殷实的希望。走出家门,步入原野,那一坡坡、一山山、一洼洼的翠绿,草木葳蕤,河水盈满,生机盎然,如同一种热切的情绪。秧青了、豆子结荚了、梅杏半黄了……黄莺深唱,杜鹃啼血,布谷催耕。柳浪闻莺,空山鸟语,雨巷燕啼,这也许是人世间最为难得的景致吧。更为撩拨乡愁的是,身居异地他乡,我竟能听到儿时最熟悉的蛙声虫鸣,它们就像儿时的玩伴,与我一起吟唱初夏的到来呢。你说说,哪一个季节能与初夏媲美?“绿肥红瘦”是这个时节最为突出的。春生、秋收、冬藏,只有夏是豪情勃发、欣欣向荣的季节。
初夏,疯狂般的涅槃。这时节,人们养精蓄锐,孕育希冀。瞧,来来往往的人群,或着薄衫,或着半袖,从容自若地穿梭在天地之间,每一个人,都在为自己的生计而奔波着,忙碌着。或许工资卡里的数字增速缓慢,或许拼命工作却遭到批评,也或许挚爱的人却成陌路,喜欢的工作却不想要你,即便是希望一次次化为泡影,即便是平日受到委屈或挫折,可生活总要继续,一切都可重新开始,未来可期。再回头看,那些曾以为过不去的坎,无法面对、让人窒息的各种难题,随着时间流逝,如今也已变得风轻云淡。所以说,只要心中有梦想,就有希望。只要为梦想而努力奋斗,每一个人都可以比昨天的自己更优秀,更强大,更精彩。
“晴日暖风生麦气,绿荫幽草胜花时。”初夏时节,微风正暖,晴日正酣,植禾疯长,麦香飘逸,殊有情味,绿荫幽幽,花草媲美,点缀成光阴里一幅妙曼无比的画卷。初夏时节,不瘟不火,不疾不徐,暗香浮动,无论城市还是乡村,到处洋溢着一种无处不有的暗香。这种暗香从高大葱茏的林木传来,从低矮茂盛的花草传来,从碧波荡漾的河湖传来,从看不见的大地深处传来,特别是在一场雨后,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令人痴迷留恋。初夏时节,带点俏皮温馨,就像一首优雅清婉的小曲,轻盈若举,丰润从容,安静唯美。她虽似“昙花一现”,却妙不可言,令人沉醉。
拉着父母去赶集
□朱超群
最近在网上刷到很多关于老家人去附近的乡镇赶集的视频,晚上和母亲打电话的时候,我特意问她,有没有也去凑个热闹?母亲笑着回我,说父亲倒是有提议一起去逛逛,但她否决了,现在年纪大了,不比以前,哪还有那精力东奔西跑,可别回头累坏了身子。
母亲的话让我心头一颤,记忆里,我小的时候,母亲可是很喜欢赶集。那时候,邻近乡镇已经兴起赶集诸事,偏偏我们镇上没有。母亲常感遗憾,一来她生性喜欢热闹,又说开春里的赶集,刚好家里还没多少农活可忙,逛个集市,见个亲朋,再好不过;二来,母亲节俭,她总感觉集市上的东西便宜,可以用最少的钱买到更多的东西。由此,我小时候没少跟着母亲赶集,母亲为我买衣服,买好吃的,以至于很多年里,我对赶集的期待不亚于对新年的期盼。
可以说,一直以来我的内心里是有个赶集情结的,我相信母亲也是。可到固定的日子,母亲还总是要念叨一句:“今天是赶集的日子呢。”记得半个月前,母亲还提起,还有多少天就到邻近哪个镇赶集的日子了……这样念叨着记挂着赶集,我相信她内心一定是希望去的。
于是,我问清楚赶集持续的天数,看到刚好连着周末,赶紧一家三口往老家赶。离老家还有一段路,我便让妻子给母亲打电话,让她早做准备。母亲在电话那头喊,说在城里为何还想着赶集,如果是为了她,大可不必。
我赶紧告诉母亲,我也想赶集,咱一家人一起去,热闹。等我们到家,父母已经准备妥当,稍微聊了几句,我们便出发去目的地。时移世易,那时候跟在母亲屁股后面等着母亲买糖买玩具的孩子,现在已经可以用自己赚的钱给母亲买喜欢的东西了。虽然随着网购的兴起,其实集市的好多东西已经不尽如人意,但不得不承认,旧时的那种快乐好像扑面而来。在人潮中,我们看这个店铺看那个店铺,目光所及,皆是欣喜。我给家人买饮料,买各自喜欢的水果。时不时地停下来,妻子陪着母亲在一起问价、砍价;我陪着孩子啃冰淇淋、买玩具,更陪着父亲一起“铁圈套大鹅”,甚至在大树荫下一边休息,一边看着他用多年的棋艺挑战“残局”……
快乐的时光总是容易飞逝。看午饭的时间到了,我告诉母亲已经订好了一家饭店。母亲听着一下子感慨,说原本自己年纪大了,怕走不动,都没敢想来赶集,这会儿既玩了,也吃了,真真是享儿子的福了。我听着不由得笑了,心里却一下子变得坚定,父母要的不多,且从来容易满足,但身为他们的儿子,想对他们好,想陪伴他们,我相信未来我会做得更好。
来源 | 羊城晚报
责编 | 朱光宇